

作者:劉余莉 鄧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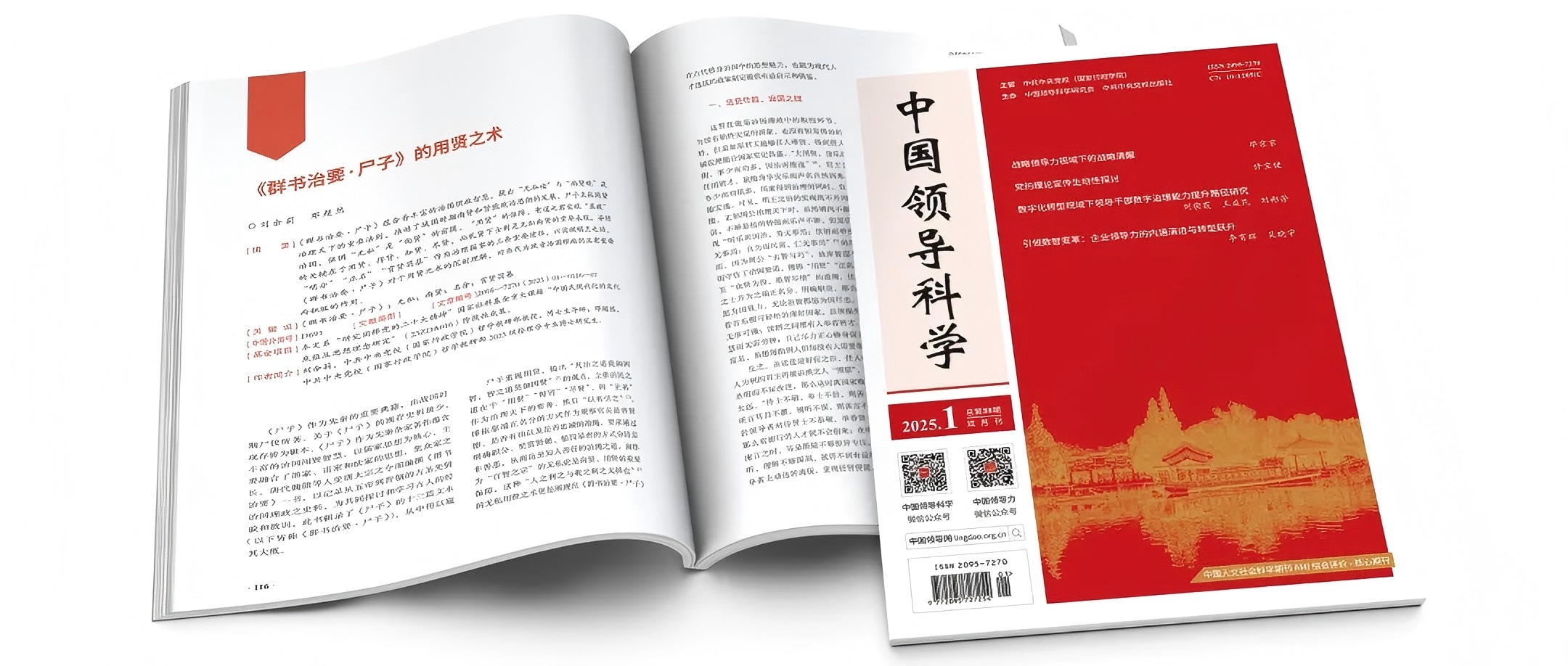
摘 要:《群書治要·尸子》蘊含著豐富的治國理政智慧,提出“無私論”與“尚賢觀”是治理天下的重要法則,推動了戰國時期尚賢和賢能政治思潮的發展。尸子主張因賢治國,強調“無私”是“尚賢”的前提、“用賢”的保障,有道之君實現“至政”的關鍵在于用賢、得賢、知賢、盡賢,而禮賢下士則是無私尚賢的重要表現,并將“明分”“正名”“賞賢罰暴”作為治理國家的三條重要途徑,以實現明王之治。《群書治要·尸子》對于用賢之術的深刻理解,對當代為政者治國理政仍具有重要而積極的作用。
關鍵詞:《群書治要·尸子》;無私;尚賢;名分;賞賢罰暴
《尸子》作為先秦的重要典籍,由戰國時期尸佼所著。關于《尸子》的現存史料極少,現存皆為輯本。《尸子》作為先秦雜家著作蘊含豐富的治國用賢智慧,以儒家思想為核心,主要融合了墨家、道家和法家的思想,集眾家之長。唐代魏徵等人受唐太宗之令而編撰《群書治要》一書,以記錄從五帝到晉朝的古圣先賢治國理政之史料,為共同探討和學習古人的經驗和教訓,此書輯錄了《尸子》的十三篇文本(以下皆稱《群書治要·尸子》),從中得以窺其大概。
尸子重視用賢,提出“凡治之道莫如因智,智之道莫如因賢”[1] 的觀點,主張治民之道在于“用賢”“得賢”“盡賢”,將“正名”作為治理天下的要務,然后“以名引之”[2] ,即依靠端正名分的方式作為觀察官員是否賢德、是否有功以及是否忠誠的準繩,要求通過明確職分、獎賞賢德、懲罰暴虐的方式分清是非善惡,從而達至知人善任的治理之道。而作為“百智之宗”的無私論是尚賢、用賢的重要保障,這種“人之利之與我之利之無擇也”[3] 的無私用賢之術更是展現出《群書治要·尸子》在古代修身治國中的思想魅力,也能為現代人才選拔的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啟示和借鑒。
一、選賢任能,治國之紐
選賢任能是治國理政中的樞紐環節。因為沒有始終安定的國家,也沒有恒常得治的百姓,但是如果君王能夠任人唯賢,得到賢人的輔佐便能讓國家安定昌盛。“夫用賢,身樂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國治而能逸”[4] ,君王善于任用賢才,就能身享安樂而聲名自然到來,事務少而功績多,國家得到治理的同時,自身也能安逸。可見,明王之治的實現離不開用賢使能。正如周公治理天下時,雖然酒肉不撤于桌前,不解懸掛的鐘鼓而樂聲不斷,但是仍能實現“聽樂而國治,勞無事焉;飲酒而舉賢,智無事焉;自為而民富,仁無事焉”[5] 的治理局面。因為周公“去智與巧”,放棄智謀與機巧而守住了治國要道,懂得“用賢”“正名”能達至“眾賢為役,愚智盡情”的道理,任用賢良之士并為之端正名分、明確職責,那么他們皆愿為國效力,無論愚智都愿為國盡忠,君王聽著音樂便可輕松治理好國家,雖欲操勞但是卻無事可做;飲酒之間便有人舉薦賢才,雖有智慧而無需勞神;自己盡力正心修身而百姓自然富足,雖想幫助別人但卻沒有人需要幫助了。
反之,親近逢迎奸佞之臣,任人唯親、任人為利的君主將被諂諛之人“圍獵”,會自以為圣明而不知改進,那么這時離國家敗亡也不會太遠。“待士不敬,舉士不信,則善士不往焉;聽言耳目不瞿,視聽不深,則善言不往焉”[6] ,若領導者對待賢士不恭敬,舉薦賢士不信任,那么有德行的人才就不會前來;在聽取賢才的諫言之時,耳朵眼睛不夠驚異專注,所看、所聽、理解不夠深刻,就得不到有益的言論。領導者主動遠奸離佞,重視任賢使能,便能成就盛世偉業。《群書治要·魏志下》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有卓越的君主必能任用卓越的大臣,有卓越的大臣必能建立卓越的功績,因此選賢任能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國家的興衰成敗。
《韓詩外傳》中將人才分為四個等級:一個人的智慧才能像源頭活水般源源不斷,他的行為可以為大眾做表率,此類人可以譽為“人師”;一個人的智慧可以砥礪磨煉人,行為可以輔助人,此類人可以稱為“人友”;一個人能嚴格按照法律行事,奉公守法,忠于職守而不為非作歹,此類人可以稱為“人吏”;一個人在他人面前一味討好對方,使人高興,別人一呼喊,他便像奴隸一樣連聲答應,這類人被稱為“人隸”。上等的君主以“師”為輔佐,中等的君主以“友”為輔佐,下等的君主以“吏”為輔佐,但是如果以“隸”為輔佐的君主將會使國家危亡。由是,應警惕“人隸”之臣帶來的禍患,因為尸子認為“夫禍之始也,猶熛火蘗足,易止也;及其措于大事,雖孔子、墨翟之賢,弗能救也。”[7] 禍患剛開始的時候,就好像火災剛發生、新芽剛長出,容易制止,但是等釀成大禍,縱使孔子、墨翟這樣的圣賢在世也是無法挽救的。因此,有遠見卓識的君主懂得防患于未然,能重用那些以道義教化百姓、以道德引導國君的賢良之人作為國之重臣。
當然,此處所說的賢良之人并非由于貴其爵列、良其先故,即不是依據他是否有高官厚祿或者顯赫的祖先作為評判標準,而是特指那些德行、意志卓越之人。春秋時期,擔任司城之官的子罕在出行時,遇到了乘地典守封疆的官員便馬上下車,跟隨他的仆人當時認為乘地封人只是個小官而已,不理解子罕下車原因,子罕便跟他講道:“古之所謂良人者,良其行也;貴人者,貴其心也。今天爵而人,良其行而貴其心,吾弗敢不敬乎?”[8] 子罕指出,古人所認為的賢良之人是指這個人行為良好,所說的高貴之人是指這個人心地高尚尊貴,如今上天賜予此人以天爵,使其行為賢良、心地高貴,自己又怎么敢不尊敬他呢?由是,高貴并不是指高官厚祿,賢良也不在于是否有顯赫的祖先,反倒是“比意志”“比德行”[9] ,以比較他們的志向思想和道德操行作為選賢舉能的真正標準。如此,明君通過任用這類賢良之才,那么全國上下便能接受圣賢教誨而達至人人向善,國家亦可安定太平。
二、無私尚賢,公心識賢
無私為本,仁心察賢。尸子強調“無私”是“尚賢”“用賢”的根本前提,提出“治天下有四術: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10] ,尤其在“無私”和“用賢”方面有其獨到見解,兩者密切相關,強調了一個核心思想——“誠愛天下者得賢”,即賢明的君主以無私之心兼愛天下,這種仁愛和無私使得他能夠發現真正的賢德之士并善于任用賢才,如此便可達至“身樂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國治而能逸”[11] 的治理效果,君主就能身享安樂而聲名自然到來,事務少而功績多,國家得到治理而自身也能安逸
但是“夫士不可妄致也”[12] ,治國的賢才不是隨便就能得到的,真正的賢士易失難得。《晏子春秋》中記載,晏子將人才分為三等:最上等的賢德之人最難出仕為官,并且即使出仕之后也最易隱退;次一等的人更容易出來做官,但是也容易退出;而最下等的人則最容易出來做官,且很難被罷退。這是因為賢德之人依靠道義而出仕,一心輔佐君王只為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的安定與幸福,但是如果沒有賢明的君主,則很難被舉薦,即使入仕,若發覺自身無法發揮作用,仍然容易退出官場。因此,無私是尚賢的根本條件。
“無私,百智之宗也”[13] ,大公無私是一切智慧的根源,是古代君主治理國家的重要道德準則。圣明君王會效法天地無私的大德,如慈母般充滿仁愛與關懷對待人民,更秉持著“愛天下欲其賢己也”[14] 的無私之心重視賢良之士。這里的“無私”不單純是道德上的超然之境,更是一種政治智慧和深刻洞見。因為只有不摻雜個人私利的領導者,才能公平、公正地選拔和任用賢才。作為政治倫理中重要一環,圣明的君主要做到“無私于物”[15] ,不僅要以無私之心愛護百姓,更要在國家大事上以公正無私的態度對待每位賢能之士。《尸子·廣》中就“公私之辯”進行了生動比喻:私心如同站在井中觀星,所見寥寥無幾;而無私則如站在山丘上觀星,視野開闊。[16] 這說明領導者如果心中充滿私欲,他的視野和判斷力會受到極大局限;而無私者則能夠放眼大局,清楚地看到事物的全貌,從而做出正確的判斷。所謂“圣人治于神”[17] 亦是如此,圣人憑借心中的公正無私用賢治國,便能事半功倍。
以身作則,樹立風范。禮賢下士不僅是一種治國方略,更是一種榜樣力量,君主通過禮賢的行為樹立了對待人才的標準,影響著整個國家的政治文化。賢君以“輕身”示賢,意在通過自己的謙遜態度,激勵更多賢才主動參政議政,為國家出謀劃策。同時,君主的禮賢行為也為官員和民眾樹立了道德標桿,營造了尊重賢才、崇尚德行的社會氛圍。這種以身作則的領導方式,極大地增強了賢才對國家的忠誠與責任感,賢才不僅感受到君主的信任和尊重,還看到了自己能夠為國家貢獻力量的價值。
一方面,賢才是國家治國安邦的根基,而禮賢下士是賢君最基本的政治態度,也是無私的重要表現。“古者,明王之求賢也,不避遠近,不論貴賤,卑爵以下賢,輕身以先士。”[18] 古代明智的君王為國家尋求賢良人才,不論關系親疏,不管地位尊卑,都會放下自己的爵位來迎接賢良人才,降低自己的身份來善待有德士人。君主對待賢才的態度,往往決定了國家的興衰。這種道德要求是無私精神的延續,體現了君主對人才的重視和對國家未來的責任感。因此,君主必須放下自己的身段,以謙虛的態度去接納和求賢,用“輕身”的方式來表示對賢士的尊重和誠意。這種姿態有助于消除賢才的顧慮,使他們敢于為國效力,并愿意貢獻自己的智慧。另一方面,賢才在為國效力的過程中,更需要得到君主的尊重和信任,君主要待士以敬、舉士以信,這種信任與支持正是源于君主的無私之心。“敬人者,人恒敬之”,這種無私體現在君主以禮義態度尊重讀書人的人格,靠德行感召賢能之士。正所謂“下士者得賢,下敵者得友,下眾者得譽”[19] ,君王謙恭地善待人才便能得到賢才,謙卑地對待對手才能化敵為友,謙虛地對待大眾才能得到聲譽。
春秋時期,齊桓公之所以能使“齊國大安”,最關鍵的是尊重管仲,并因此得到了管仲的輔佐。齊桓公任用管仲治國,管仲認為“賤不能臨貴”,桓公便拜其為上卿;隨后管仲又提出“貧不能使富”,桓公就把齊國市場一年的稅收賜給管仲;但是國家仍未得到治理,管仲就說“疏不能治親”,齊桓公仍然尊重他的建議,并且給了他很好的待遇,尊管仲如同父親一般,將其立為“仲父”,之后齊桓公九合諸侯,稱霸天下。由此觀之,無私之心能促使領導者打破傳統的等級觀念和親疏界限,真正做到“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20] 。真正的圣君不會因為個人的感情而妨礙賢才的選拔和任用,也不會因為賢才出身卑微而忽視他們的才能,更不會因為賢才是自己的親戚或敵人而有所偏袒或排斥。相反,圣明君主會以平等的態度任用賢能之士為國效力,踐行“賢者盡,暴者止”[21] 的治民之道。這種不偏不倚的無私態度,使得圣人能夠廣泛接納賢才,達成“身無變而治,國無變而王”[22] 的治理目標。因此,君主不以身份、權勢自居,而是真誠地對待賢良之士,視他們為國家的寶貴財富,以無私之心禮賢下士,此之謂賢能政治得以實現的關鍵。
三、正名明分,賞賢罰暴
治國要重賢。尸子提出“國之所以不治者”有三方面的原因,即不知用賢、不能得賢、不可盡賢。相應也提出了“明分”“正名”“賞賢罰暴”這三條治國之道,即“明分則不蔽,正名則不虛,賞賢罰暴則不縱,三者治之道也。”[23] 明確職分能夠讓人完全看清是非善惡,端正名分能幫助分清是非善惡,獎賞賢德、懲罰暴虐就不會放縱,這三者是治國之道。反之,“是非不得盡見謂之蔽,見而弗能知謂之虛,知而弗能賞謂之縱,三者亂之本也。”[24] 不能完全看清是非善惡,叫作糊涂;分清了是非善惡卻不能知人善任,叫作徒勞;看清是非善惡又能知人善任而不能實施獎賞,叫作聽任放縱,這三方面是國家動亂的根本。事實上,賢能一直都在,更關鍵的是對賢良之士的發掘和如何選賢用賢。正所謂“為人君者以用賢為功”,作為君王以任用賢才為功勞,用賢得當便可以實現“至政”。因此,通過“明分”“正名”“賞賢罰暴”的途徑用賢、得賢、知賢、盡賢,便能實現極清明的政治。
(一)正名去偽,事成若化
“治天下之要,在于正名。”[25] 治理國家的關鍵在于“正名”,端正各自的名分,使之名實相符,以能夠知人善任。所謂“正名去偽,事成若化”[26] ,正名不僅可以幫助君主判斷是非,還可以確保國家各項事務順利進行。在“以實覆名”[27] 的前提下,愚智之人皆能盡其所能,事情自然得以成就。反之,尸子指出,倘若“是非不得盡見”,即無法辨清善惡,就會導致糊涂;“見而弗能知謂之虛”,即便看清是非卻無法知人善任,則是徒勞無功;“知而弗能賞謂之縱”,如若知人善任卻不實施相應獎懲,則會導致社會混亂無序[28] 。因此,正名不僅是國家治理的根本,也確保了社會秩序的穩固。名實相符的正名思想被用作治國理政的基本原則,通過正名,國家不僅能夠分辨是非、賢愚,還能通過合理的獎懲機制確保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名實相符是確保國家治理和社會運行順利的重要保證。
正名之用,名實相符。“正名”很早就經由孔子提出,強調了名實相符的重要性。《論語》中載,“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29] 。尸子承襲并發揚了孔子的正名理論,這一理論在治理國家和規范社會行為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正名”一方面意在確保名與實相符,意味著在社會政治系統中,名稱、身份和實際職責必須對應得當;另一方面,它強調應當盡量以清晰的語言、規則和定義來指導治理、政治和人際關系。“正名去偽,事成若化”道出了正名的根本作用,即通過正名去除虛偽,名實統一后,事務的開展將會變得順理成章,甚至達到“化成”的程度,即事物發展自然而然,無須強力干涉或操控。“去偽”指的是去除名實不符的現象,確保職責、權利、地位等與實際情況一致,這樣社會和國家的治理才會更加順暢。因此,正名不僅是一種理論,更是落實政治實踐、確保治理成功的關鍵手段。當名與實相符時,無論是有智慧的人還是普通的百姓,都能夠在各自的崗位上盡職盡責,發揮最大的能力。正名不僅幫助統治者區分善惡、識別賢能,更在于通過明確每個人的職責,確保他們能夠根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行事。所以,名實相符的核心思想在于為賢良之士提供展現才華的舞臺,正名能夠幫助國家識別和任用賢能之士,賦予與其才能相符的職位,使他們在合適的位置上通過自己的智慧和經驗充分發揮作用。
正名之效,決斷是非。正名思想的一個核心作用就是幫助統治者在政治事務中做出明智的決策。君主通過正名來判斷是非,以知人善任,這不僅關乎國家事務的成敗,也決定了國家的長治久安。由于正名要求名與實相符,這也正為獎罰制度提供了依據。“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罪,措準則地之險者有罪,審名分則群臣之不審者有罪”[30] ,意思是說,用墨繩來衡量木頭,彎曲的木頭就不符合標準,放置水平儀來測量地面,地勢不平的地方就不能合乎標準,審核名實是否相符,那些不嚴謹慎重的大臣就有了罪過。這說明,即便君主能夠通過正名識別賢能之士,如果不能合理安排他們的職務,那也是一種失職;如果任用了賢才卻沒有相應的獎懲措施,也是不正之道。因此,正名可以通過決斷是非對錯來識別人才,并幫助國家建立一套公平的賞罰機制,使得社會秩序穩定,確保國家的有序運行。
(二)明分不蔽,知人善任
“明分”的重要目的就是通過合理分配職務來確保賢良之士能夠各盡本分、發揮才能。君主在朝堂聽政時,應做到“聽朝之道,使人有分”[31] ,這里的“分”是指“本分、職分”。君主對待賢良之才,應該明確并合理分配職務,只有當每個人的職責明確,才能做到各盡其才,都能在最適合自己的崗位上發揮作用,真正實現國家治理的高效運作。所以,圣人“裁物以制分,便事以立官”,即通過裁定事物并使萬物遵從各自的本分、職責,根據國家事務設立官職,使得“君臣父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疏,皆得其分曰治”,如此君臣父子等“五倫”關系各盡本分便能實現天下大治,做到“愛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動得分曰適,言得分曰信”,即愛心、施舍、思謀、行動、言論皆能切合自己的本分便是做到了仁、義、智、適、信,這樣“皆得其分而后為成人”,各方面盡到自己本分后就能成為一名德才兼備的人。[32]
由此看出,相對于儒家注重內在的“成仁”,尸子所主張的“成人”主要取決于倫理關系和外在行為是否“皆得其分”。在尸子看來,“分”是“德”“義”“禮”的衡量標準,他提出“德者,天地萬物得也;義者,天地萬物宜也;禮者,天地萬物體也。使天地萬物皆得其宜,當其體者,謂之大仁”[33] ,意思是說,“德”是天地萬物各得其所、各安其位,自然運轉,“義”是天地萬物適宜,“禮”就是天地萬物的運行合乎規矩,使天地萬物各自按其規律發展運行、井然有序,就叫作“大仁”。由此可見,天地萬物遵照“德”“義”“禮”而發展的終極目的就是“得分”,“分成”則“天下之可治”,天下能夠得以治理的原因就是明確了各自的職分。
“明分則不蔽”[34] ,即分清職責、合理分工,就能避免賢才被埋沒。只有當每個人的職責明確,才能做到知人善任,確保國家治理的順利進行。反之,如果“好士,且知之也,好而弗知,則眾而無用也”[35] ,君主不能分清賢才的職責,或者沒有合理安排賢才的職務,就會導致即使有賢能之人存在,他們也可能不會充分發揮出自己的全部才能、履行好自己職責的尷尬局面,國家的治理也將因此陷入困境。由是,君主在任用賢才時,必須明確他們的職責分工,使其都在適合自己的位置上工作,發揮其最大作用。此外,明分不蔽還強調了君主用賢的公正性。君主不僅要在形式上禮賢下士,更要通過合理的分工,讓賢才在實際工作中發揮才能。歷史上,唐朝的貞觀之治之所以能夠取得輝煌成就,正是因為唐太宗在用人時能夠做到“知人善任,各盡其才”,通過合理的分工和信任,使得賢才得以在各自的崗位上為國家做出貢獻。因此,“明分”不僅是治國的基本原則,也是確保賢才能夠充分施展才能的重要保障。
(三)賞賢罰暴,賢盡暴止
賞罰分明強調了君主對賢才的尊重和重視。這里“賞賢罰暴”有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方面,獎賞賢德、懲罰暴虐之人。對待群臣要賞罰分明,“賢則貴之,不肖則賤之;治則使之,不治則愛之,不忠則罪之”[36] ,重用有賢德、有功績的人才,罷免無德之人,愛護沒有政績之人,懲罰不忠之人。另一方面,獎賞舉薦賢才之人,懲罰舉薦不賢能的人。古代的宰相不一定是最有能力的人,但一定能慧眼識人,“為人臣者以進賢為功”[37] ,作為臣子要把舉薦賢才作為功績,推舉德能超過自己的賢能之士。若“使進賢者必有賞,進不肖者必有罪,無敢進也者為無能之人”[38] ,即讓舉薦賢才的人一定能獲得褒獎,讓舉薦不賢的人一定遭到懲罰,對于那些不敢舉薦的人視之為無能的官員,這樣必定會涌現出更多舉薦賢才之士的人。
賞罰分明體現了治國理政中的公平與正義。賞賢罰暴作為治國的基本方式之一,也是賢才安心從政的前提條件。如果賢良之士的才能得不到應有的認可,或者他們的努力沒有得到相應的獎勵,賢才就會失去為國效力的動力;同樣,若是不賢之人得不到應有的懲罰,國家的賞罰制度也將失去威信,賢才的積極性也會因此受到打擊。反之,與賢能者相對的是暴虐者和無德之士,暴虐者往往通過名實不符的方式獲得不應有的權力和地位,導致國家秩序混亂、社會道德淪喪。因此,賞賢罰暴的原則不僅能夠有效利用賢能者的才華,獲得更多的賢良之士,還能制約那些濫用權力的人。通過賞賢罰暴的方式來規定權力的合理分配和職權的明確劃分,可以有效限制這類人的行為,使其無法對國家和社會造成破壞。圣王在治理中如果遵循“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是則有賞,非則有罰”[39] 這一原則,即是非根據名分和實際是否相符來判斷,獎賞與懲罰需要根據是非來辨別,如果是正確的就給予獎賞,錯誤的就給予懲罰,如此暴虐者的行為不僅會被制止,還將通過公平的獎懲機制受到應有的懲罰。當國家的獎懲制度健全時,暴虐者的行為將會被零容忍,他們的權力將被削弱甚至被剝奪,這種制度不僅是對個體行為的約束,更是對國家秩序的有效維護。在歷史上,許多成功的君主都深諳賞罰分明的重要性。秦始皇通過法家的嚴明賞罰制度,成功地實現了統一六國的大業;唐太宗通過嚴格的賞罰制度,確保了貞觀之治的持續繁榮。這些歷史經驗表明,任人唯賢不僅需要君主的謙遜態度,更需要通過公正、合理的制度安排,確保賢才的才能得到充分發揮。
總之,圣王治道,無為而治。在古代思想體系中,圣王治理的最高境界就是“無為而治”,其實現離不開明智的用賢之術。這與尸子提到的“明王之治民”有異曲同工之妙,即“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國治,言寡而令行”[40] ,圣明的君王領導人民,事情雖少卻能功績卓著,自身閑逸而國家卻能得到治理,言語不多但命令卻能貫徹執行。尸子認為“明王之道易行也”[41] ,通過“正名”“明分”使賢德者得以盡其所能,使得國家內部的各個階層都能夠各司其職,輔助以賞賢罰暴的原則作為激勵人才的方式,通過無私誠心感召賢良之才,當賢能者被充分利用,而暴虐者的行為被制止時,便能實現賢能政治,那么國家的治理自然而然就能達到最理想的狀態。
注 釋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30][31][32][33][34][35][36][37][38][39][40][41](唐)魏徵,等.群書治要譯注:第8冊[M].北京:中國書店,2012:3057,3050,3055,3056,3043,3040,3033,3028,3028,3055,3056,3040,3055,3055,3056,3061,3033,3039,3040,3059,3050,3043,3050,3050,3052,3052,3044,3050,3048,3050,3042,3067,3050,3048,3050,3052,3052,3048,3043,3043.
[29](春秋)孔子.論語[M].北京:團結出版社,2020:211.
【注:原載《中國領導科學》2025年第一期。作者劉余莉,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鄧超然,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教研部2023級倫理學專業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