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劉余莉 聶菲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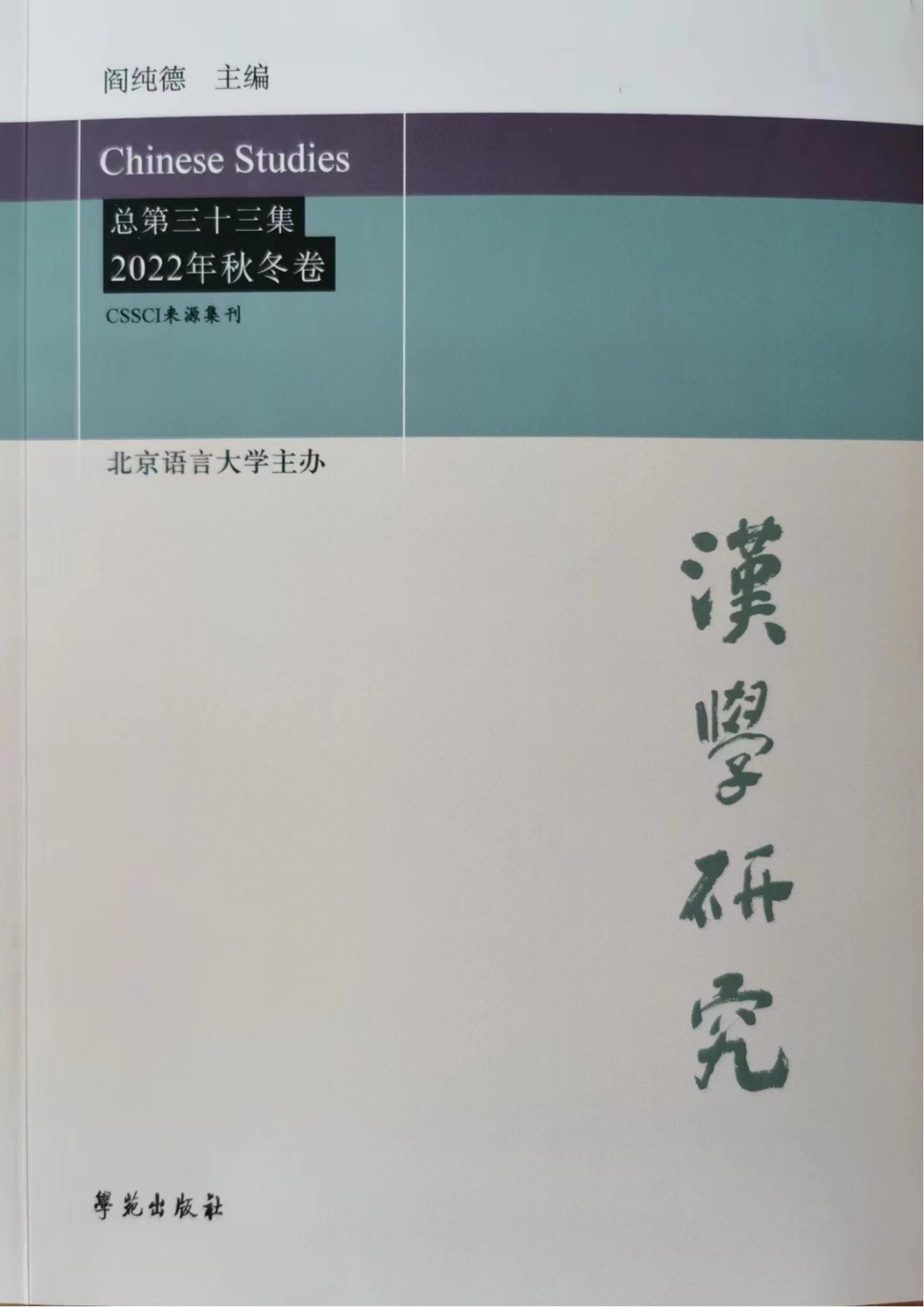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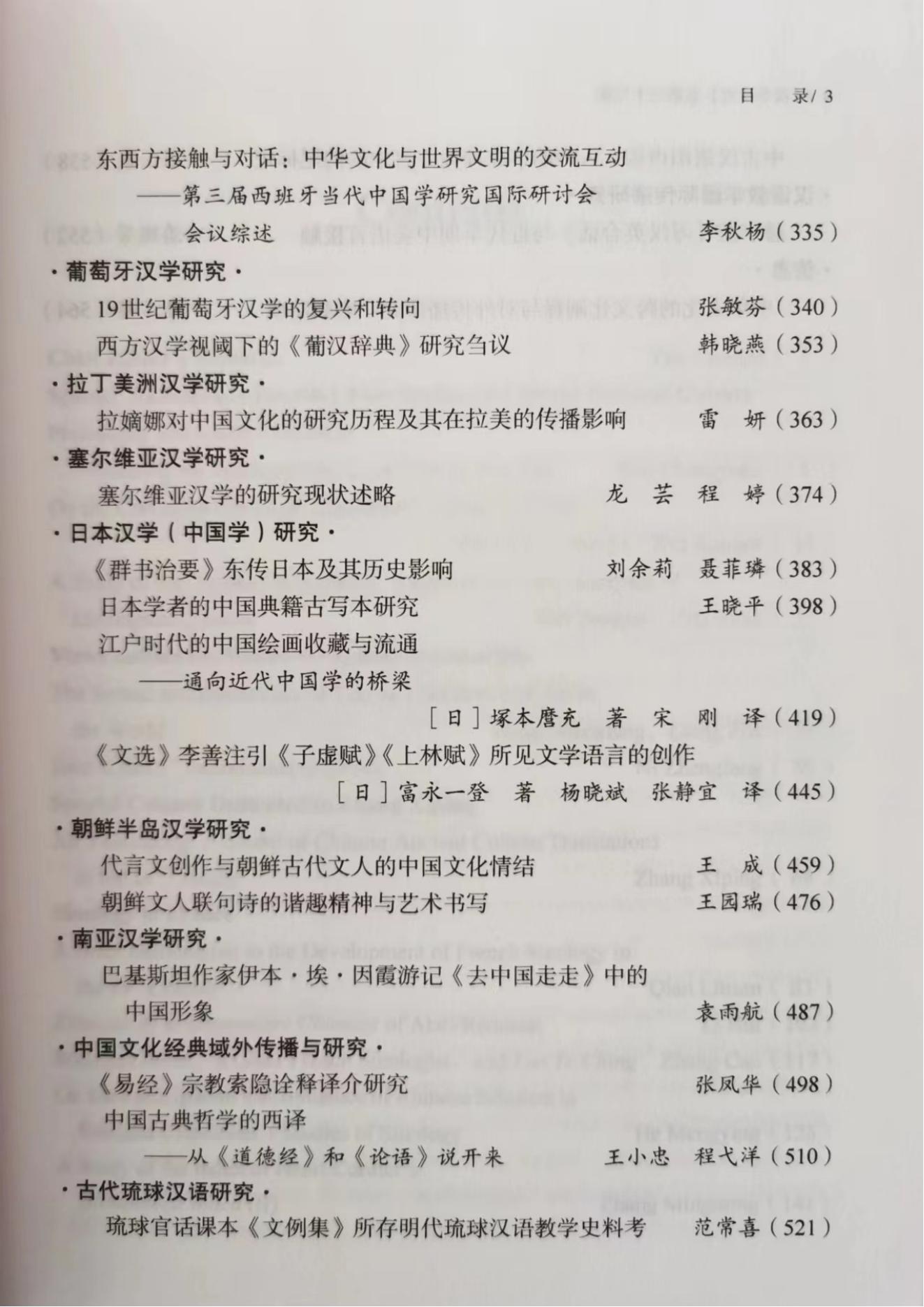
摘 要 :《群書治要》是一部匯集了六經至諸子中古圣先王治國理政智慧精華的匡政巨著,為大唐盛世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唐玄宗天寶年間,日本遣唐使將其攜回。由于《群書治要》重要的思想價值以及與盛世產生的內在聯系,這部書被歷代皇室、公卿所重視,并且經歷了從皇室向民間逐漸普及的流傳過程。從國家治理到思想傳播,從漢籍出版到學術研究,《群書治要》很多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群書治要》東傳日本的歷史意義還體現在,它為中國保存下了這部珍貴卻又亡佚的“帝王學”教科書,并幾次將其傳回中國,使這部治世寶典在當今時代繼續發揮“古鏡今鑒”的重要價值。
關鍵詞 :《群書治要》 東傳 日本 歷史影響
2022年習近平主席致新年賀詞時的右手邊書架上,出現了一部極其珍貴卻又鮮有人問津的經世之作——《群書治要》。其實早在2015年,這部書就已出現在習主席新年賀詞的書架上了。
《群書治要》是唐太宗為求治國良策而令魏徵等社稷之臣,以“務乎政術”“本求治要”為宗旨,整理歷代帝王治國資政史料,從五帝至晉年之間經、史、子部典籍之中,擷取有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精要,匯編而成的匡政巨著,成書于貞觀五年(631)。唐太宗閱讀手不釋卷,感慨“覽所撰書,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并賜太子諸王作為從政龜鑒。《群書治要》不僅是魏徵向唐太宗進諫的重要理論依據,也是唐太宗創建“貞觀之治”的思想源泉和理論基礎。遺憾的是,《群書治要》傳至南宋只余十卷殘帙,《元史》已不見著錄。這部書雖然在中土亡佚,但有幸在唐朝時被遣唐使攜回日本保存并流傳,成為日本學習中華文化的重要典籍。
1996年春,我國原駐日大使符浩先生通過日本皇室成員獲得一套影印天明版《群書治要》,由關學研究專家呂效祖等對其點校考譯。《群書治要考譯》的編纂受到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習仲勛老先生的親切關懷。2001年2月25日,習老先生親筆為《考譯》一書題詞“古鏡今鑒”,為繼承和弘揚這部治世寶典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指南,為其在當代的弘揚和傳播揭開了新的篇章。據統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中的用典來自《群書治要》的有82條之多。黨的十八大之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系列治國理政的新思想和新理念也都可以從《群書治要》中找到其思想淵源。
《群書治要》是中日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見證,也是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結晶。梳理《群書治要》東傳日本的來龍去脈,探究此書在日本的流傳及影響,是一項重要的學術課題,具有歷史及現實意義。
一、《群書治要》東傳日本
史料沒有明確記載《群書治要》東傳日本的時間及途徑。尾崎康認為是奈良(710—784)至平安(794—1185)初期傳入。金光一認為奈良時代天寶遣唐使(唐玄宗朝)和平安時代貞元遣唐使(唐德宗朝)攜回此書的可能性較大。筆者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深入史料進一步分析了兩次東傳的歷史時機,認為天寶遣唐使一行最有可能將《群書治要》攜回日本。
天寶遣唐使是日本第十一批遣唐使,由孝謙天皇于天平勝寶二年(750)任命,藤原清河任大使,大伴胡萬和吉備真備任副使,天平勝寶四年(752,唐天寶十一年)閏三月出發,次年天寶十二年(753)三月藤原清河敬獻方物,六月朝見唐玄宗。天平勝寶五年至六年(753—754)回到日本。金光一據《東大寺》所引《延歷僧錄》的記載分析,本次遣唐使受到了唐玄宗熱情隆重的接待,特別是副使吉備真備拜秘書監,并由朝衡(阿倍仲麻呂)任使團參觀向導,獲賜進入宮廷秘府瀏覽群書的機會,因此有了發現《群書治要》的可能。《玉海》引《集賢注記》云:“天寶十三載(754)十月,(玄宗)敕院內別寫《群書政要》,刊出所引《道德經》文。先是,院中進魏文正所撰《群書政要》,上覽之稱善,令寫十數本分賜太子以下。”據此,天寶十三年之前,唐玄宗曾閱讀《群書治要》并稱贊有加,因此下令抄寫并分賜太子以下。史料沒有記載《群書治要》錄副工作是否在遣唐使抵達之前完成,但此時朝衡已升任秘書監,又長期參與宮廷文獻管理,理應悉知《群書治要》。又因朝衡與吉備真備同為第九批即開元五年(717)遣唐留學生,關系甚篤,很可能會向吉備真備推薦《群書治要》,而作為中國文獻專家的吉備真備也很可能積極地將其攜回。綜上,金光一認為,“《群書治要》的東渡很有可能是由唐玄宗、吉備真備和朝衡的合作而成的,唐玄宗對這次使節的歡待,真備搜集和攜回中國典籍的熱情,以及朝衡對秘府藏書的知識,使得《群書治要》東傳到日本。”筆者認為金光一的推斷是合理的。
貞元遣唐使是日本第十七批遣唐使,由桓武天皇派遣,藤原葛野麻呂任大使,菅原清公任判官。貞元二十年(804)十二月藤原葛野麻呂抵達長安,貞元二十一年(805)二月離開長安。《日本后紀》卷十二恒武天皇延歷廿四年六月八日條詳細敘述了此次使團行跡。金光一認為,雖然其中并無與《群書治要》相關的記載,但是不排除《群書治要》此時東渡日本之可能,并列出了三條依據:第一,作為紀傳博士的菅原清公非常重視中國的帝王學,如果獲知《群書治要》的存在,很可能積極地將其攜回;第二,由《鄴侯家傳》所記唐德宗與李泌的對話知貞元遣唐使行時,唐秘府仍存藏《群書治要》,而且即使遭逢國喪,唐室對貞元遣唐使的款待不亞于天寶遣唐使;第三,日本皇室最早閱讀《群書治要》是在承和五年(838),與貞元遣唐使時間相對接近。
金光一所列的三條依據,第一、二條可合并為對獲得《群書治要》可能性的推測。筆者查閱史料后認為,雖然貞元遣唐使存在獲得《群書治要》的可能,但實際上可能性很小。《日本后紀》卷十二桓武天皇延歷二十四年六月八日條記錄:
廿四日,國信、別貢等物,附監使劉昴進于天子。劉昴歸來,宣敕云:“卿等遠慕朝貢,所奉進物,極是精好,朕殊喜歡。時寒,卿等好在。”
廿五日,于宣化殿禮見。天子不衙。同日,于麟德殿對見。所請并允。即于內里設宴,官賞有差。別有中使,于使院設宴,酣飲終日。中使不絕,頻有優厚。
廿一年正月元日,于含元殿朝賀。
二日,天子不豫。
廿三日,天子雍王迨崩,春秋六十四。
廿八日,臣等于亟天門立仗,始著素衣冠。是日,太子即皇帝位。諒閻之中,不堪萬機。皇太后王氏,臨朝稱制。臣等三日之內,于使院朝夕舉哀。其諸蕃三日,自余廿七日而后就吉。
二月十日,監使高品宋惟澄,領答信物來,兼賜使人告身,宣敕云:“卿等銜本國王命,遠來朝貢,遭國家喪事,須緩緩將息歸鄉。緣卿等頻奏早歸,因茲賜纏頭物,兼設宴,宜知之。卻回本鄉,傳此國喪,擬欲相見,緣此重喪,不得宜之,好去好去者。”事畢首途,敕令內使王國文監送,至明州發遣。
由上述記錄知,貞元二十年(804年,延歷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使團朝見唐德宗,德宗對使團一行設宴、賞賜,“所請并允”。貞元二十一年(805)元旦,使團參加朝賀,再次見到德宗。正月二十三日,德宗病逝。國喪期間使團參與悼念。二月十日,唐皇室“賜纏頭物,兼設宴”,隨后使團離開。可見,使團在長安遭逢國喪,僅有短暫停留,未有較多活動,相比天寶遣唐使之行去之甚遠。
筆者認為,使團兩次朝見唐德宗,第二次朝見屬于元旦朝賀,第一次是正式的使團朝見,因此更可能獲得《群書治要》。獲得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使團向德宗提出請求,一種是德宗直接賞賜。第一種方式的前提是日本使節預知《群書治要》的存在,并且知道此書的價值,但目前尚未查得相關史料。第二種方式的前提是唐德宗對《群書治要》有所了解,且當時朝廷有副本存在。《玉海》引《鄴侯家傳》記載了李泌與唐德宗的對話:
上曰:“朕欲知有古政理之要,而史籍廣博,卒難尋究,讀何書而可?”
對曰:“昔魏徵為太子略群書之言理道者,撰成五十卷,謂之《群書理要》,今集賢合有本。又肅宗朝宰相裴遵慶撰自上古已來至貞觀帝王成敗之政,謂之《王政紀》,凡六十卷。比寫本送臣,欲令進獻于先朝,竟未果。其書見在,臣請進之,以廣圣聰。”
上曰:“此尤善也,宜即進來。”于是表獻。
由對話可知,當時集賢院尚存《群書治要》,但經過“安史之亂”,唐玄宗朝錄副的《群書治要》劫后余存數量未知,難以判斷是否尚存副本。而且德宗最終選擇的是閱讀《王政記》,因此可能并不了解《群書治要》,主動賞賜的可能性也就不大了。總之,第一次朝見德宗時,雖有“所請并允”并設宴賞賜的記載,但是獲得《群書治要》的可能性非常有限。
金光一的第三條依據是日本皇室最早閱讀《群書治要》的時間在承和五年(838),與貞元遣唐使時間相對接近。筆者認為此說有待商榷。《日本の年號》“延曆”條云:
延曆の出典は不詳であるが、『群書治要』卷二六に「民詠德政、則延期歷」とある(その原拠は『三國志』魏書二五高堂隆伝。「歷」と「曆」とは通用。95永曆の項參照)。
據此,桓武天皇年號“延歷”有可能出自《群書治要》,那么“延歷”之前,《群書治要》就應該已傳入日本。而貞元遣唐使之行在延歷二十三至二十四年(804—805),就不可能是首次將《群書治要》攜回了。此外,承和五年(838)是史料記載的天皇最早閱讀此書的時間,但未必就是此書被閱讀的最早時間。如果“延歷”有可能出自《群書治要》,就可能存在天皇或臣子閱讀此書而未記載的情況。天寶遣唐使于天平勝寶五年至六年(753—754)回到日本,此后不到30年即延歷元年(782)。而貞元遣唐使回國的時間(805)與承和五年(838)相距卻有33年。因此筆者認為,日本皇室最早閱讀《群書治要》與貞元遣唐使回國的時間相對接近是值得商榷的。
結合《日本后紀》對貞元遣唐使之行的記載及日本學者對“延歷”年號出處的推測,筆者認為,貞元遣唐使攜回《群書治要》的可能性很小。天寶遣唐使之行,無論是當時唐皇室還是日本使團的情況,都有利于書籍傳播,因此是最有可能將《群書治要》攜回日本的,即《群書治要》于奈良時期天平勝寶五年至六年(753—754)傳入日本。
二、《群書治要》在平安時期的流傳及影響
《群書治要》傳至日本后,日本天皇將其奉為圭臬,并確立了系統講授此書的傳統。史籍記載,平安時期有四位天皇閱讀過此書。
仁明天皇是日本文獻中首次記載閱讀此書的天皇。《續日本后紀》第七卷記載,承和五年(838)六月壬子(廿六),“天皇御清涼殿,令助教正六位上直道宿禰廣公讀《群書治要》第一卷。有五經文故也。”仁明天皇熱愛中國文化,“柱下漆園之說,《群書治要》之流,凡厥百家,莫不通覽”。這一時期也成為日本皇室傾向中國文化的極盛時期。
清和天皇仰慕唐太宗開創“貞觀之治”,意欲效仿,于是踐祚翌年,天安三年(859)四月十五日庚子,改元“貞觀”。《日本三代實錄》后篇卷二十五記載,貞觀十六年(874)閏四月二十八日丙戌,“頃年天皇讀《群書治要》。是日御讀竟焉。”貞觀十七年(875)四月二十五日丁丑也有天皇閱讀此書的詳細記載。
尾張藩校督學細井德民《刊〈群書治要〉考例》云:“謹考國史承和、貞觀之際,經筵屢講此書,距今殆千年。”朝散大夫國子祭酒林信敬《校正〈群書治要〉序》云:“我朝承和、貞觀之間,致重雍襲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講究此書之力。則凡君民臣君者,非所可忽也。”這充分說明《群書治要》在成就日本平安前期繁榮局面中所起的作用,也強調了大凡領導人民、事奉國君者是不可輕忽此書的。
宇多天皇閱讀《群書治要》的記錄見于現存最早的菅原道真傳記《菅家傳》:“(寬平)四年(892),……奉敕清涼殿侍讀《群書治要》。”菅原道真道德文章皆為上乘,宇多天皇贊賞有加:“右大將菅原朝臣,是鴻儒也。又深知政事。朕選為博士,多受諫正”。宇多天皇重用原道真,整肅政綱,刷新政治,后世稱為“寬平之治”。寬平九年(897)宇多天皇讓位于醍醐天皇時,贈《寬平御遺誡》作為天皇之“金科玉條”。《遺誡》中有“天子……唯《群書治要》早可誦習”的勸勉之辭。
醍醐天皇謹遵父訓。《日本紀略》第三(后編)記載:昌泰元年(898)二月二十八日戊辰,“式部大輔紀長谷雄朝臣侍清涼殿,以《群書治要》奉授天皇。大內記小野朝臣美材為尚復。公卿同預席”。醍醐天皇的臣籍皇子源高明私纂的儀式書《西宮記》將《群書治要》列為奉公之輩的設備之書。這不僅說明公卿大臣對《群書治要》的重視,也說明此時《群書治要》已不再囿于天皇及博士閱讀。
從平安中期開始,日本天皇大權旁落,但也是在這一時期《群書治要》開始走出皇宮,進入京都貴族之家,這固然有治國理政的需要,閱讀與傳抄《群書治要》一時成為京都貴族的時尚。現存最早的《群書治要》文本,便是由京都貴族“五攝家”之一的九條家代代保管的平安本《群書治要》(又稱九條家本)。
平安本于“二戰”后被發現于九條公爵府邸的一間倉庫,余13卷殘帙,抄寫于10或11世紀,是當前《群書治要》最古老的寫本,文獻價值極高。其所用紙張屬于高貴的御用材料,書寫風格優雅端正,這種風格多見于平安時代抄寫的和歌典籍,漢籍則少見,因此推測平安本《群書治要》是在特殊情況下制作。也正是由于高貴的用紙及精美的筆跡,九條家經常將卷子切割后作為珍貴的禮物獻給天皇、貴族或贈與友人,成為“古筆切”藏品,這導致平安本《群書治要》多有散佚,但也說明了其珍貴的文物價值。根據平安本《群書治要》殘簡的散佚及殘卷奧書的記載,《群書治要》不僅在當時,而且在后世有著廣泛的閱讀和傳抄,可見,《群書治要》中有關治國理政的思想在日本古代獲得了廣泛認可。1952年,平安本《群書治要》被指定為“日本國寶”。
三、《群書治要》在幕府時期的流傳及影響
鐮倉幕府(1192—1333)至江戶幕府(1603—1867)這段時期,天皇權力被架空,政治實權在幕府手中。直至明治維新,與《群書治要》相關的記載多集中在幕府。
(一)鐮倉幕府時期
幕府非常重視學問,據佐川保子,平安末期至鐮倉幕府時期,教授天皇的漢籍有《古文尚書》《古文孝經》《后漢書》《貞觀政要》《帝范》《臣規》《白氏文集》等,教授“公卿、將軍等特定貴人”的書籍除上述外,還有《春秋經傳集解》《論語》《群書治要》。
鐮倉幕府的文化遺產中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的是由北條實時創建的金澤文庫。金澤文庫是日本中世紀武家文化之代表文庫,收有日、漢典籍兩萬卷以上,素有“和漢文物之淵藪”之稱。從北條實時到其孫北條貞顯時期的寫本,是金澤文庫中最為古老的組成部分,金澤本《群書治要》亦是此時產生的珍貴典籍。
建長五年(1253),北條實時委托后藤基政抄寫了《群書治要》全帙,又命三善康有抄寫副本。文永七年(1270)十二月,原本史部多卷被焚毀,隨后根據副本進行了補抄。14世紀初,北條貞顯發現仍有一些卷子不存,便利用自己在京都任職的機會,借出藤原光經和藤原經雄(藤原俊國之子)的藏本補抄。
北條實時還委托清原氏家族和藤原氏家族的學者為金澤本《群書治要》添加了訓點。清原教隆為經部諸卷添加了訓點,并多次傳授北條實時。金澤本卷一奧書云:“建長七年(1255)八月十四日,蒙灑掃少尹尊教命,加愚點了。……同年九月三日即奉授灑掃少尹尊閣了。”說明八月十四日清原教隆加點完畢后,九月三日即開始向北條實時教授此卷。據小林芳規,傳授并不僅限于九月三日這一次,各卷末類似備忘錄風格的橫線(“讀符”)表示傳授或解讀的次數。由此可知經部各卷中,卷一傳授六次,卷三五次,卷五、六各四次,卷七、九、十各兩次。
史部訓點者是藤原氏南家的藤原茂范,以及藤原氏北家系統內麿流日野家的藤原俊國。由于史部多卷屬于補抄,因此無法知曉北條實時是否學習過。但從移錄底本奧書的內容可知對底本《群書治要》(非金澤本,而是《群書治要》其他藏本)的閱讀與傳授情況,如卷廿九奧書記載文永八年(1271)藤原經雄閱讀了此卷,卷三十奧書記載藤原經雄傳授了此卷。這說明當時對《群書治要》的學習是比較普遍的。
子部的訓點是清原教隆根據蓮華王院寶藏御本移寫的,而御本的訓點除卷冊六由清原賴葉(教隆的祖父)添加外,其他諸卷是由藤原氏式家宇合流的敦周、敦經和敦綱添加的。根據“讀符”,清源教隆將卷卅六、冊一至冊三、冊五至冊六、冊八至五十各以一次傳授給北條實時。
從金澤本奧書可知,12世紀末至14世紀初,日本皇室、京都貴族以及幕府有眾多《群書治要》藏本,而且從天皇、博士家,到幕府將軍、御家人,都對學習《群書治要》有著濃厚的興趣,不斷進行抄寫、點校、閱讀。
1333年,鐮倉幕府滅亡。此后日本經歷了室町幕府及戰國時代,時局變亂,眾多《群書治要》抄本紛紛失散,至江戶幕府德川家康時,金澤本《群書治要》成為了海內孤本(卷四、十三及二十已亡佚),這也使金澤本成為了此后諸《群書治要》版本的母本。
金澤本《群書治要》是日傳漢籍中的瑰寶。如果同時考慮年代和保存情況,金澤本《群書治要》目前是“最古的全本”,其在文獻學、文字學和中國古代治道思想方面,都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
(二)江戶幕府時期
德川幕府的將軍、幕僚等皆注重文治,尤其注重《群書治要》的閱讀和刻印,出現了慶長、元和、天明、寬政、弘化等眾多《群書治要》版本。
1.慶長一元和年間
《群書治要》能夠在江戶時期重振光輝,與德川家康的積極推動密不可分。德川家康雖出身武家,但喜文翰,確立了“文治武功”的基本治國策略。特別是認識到印書在文治中的積極作用,退居駿府后,便傾力于銅活字印刷。其實早在慶長年間,德川家康就已經開始重視《群書治要》。慶長十五年(1610)九月,德川家康下令將金澤本《群書治要》抄寫兩份,作為制定公家、武家法度的參考,并按照唐太宗編纂此書的目的加以利用。這便是慶長本《群書治要》,此本后來成為元和本《群書治要》的底本。
元和本《群書治要》是德川家康于元和二年(1616)正月十九日下令印刷的,也是家康下令印刷的最后一部漢籍。金光一據《禁中并公家諸法度》認為,元和本《群書治要》的印刷政治色彩濃厚。《法度》是關于江戶幕府與天皇及公家之間關系的法律,第一條“天皇の主務”規定天皇在各種技藝能力之中應當以研習學問為先,并援引《寬平御遺誡》云,天子雖不窮經史,但可誦習《群書治要》。然而《群書治要》此時只有金澤本這一孤本了,因此江戶幕府要流布《群書治要》,首先需要印書,這便有了元和本的刊印。
德川家康不僅下令刊印《群書治要》,還命林羅山補足《群書治要》所缺之卷。“元和元年(乙卯),先生(林羅山)赴駿府奉命監《群書治要》等刊版之事,且補足治要闕失之數卷。”或許是元和本刊印之時,林羅山補缺工作尚未完成,因此元和本《群書治要》仍為47卷。
元和本《群書治要》于元和二年(1616)五月底成書,用時四個多月,可謂非常迅速。然而在此之前的四月十七日,德川家康在駿府城猝然逝世,生前僅見部分刊印成果,遺憾未見書成。元和本也未得奉命流布于世,而是隨其他藏書一起,被分贈給家康的兒子。其中銅活字傳紀伊家,印本傳尾張、紀伊兩家。
元和本《群書治要》不僅是日本首次大規模印刷《群書治要》,而且在日本印刷史上也有著重要地位。元和本《群書治要》47卷及《大藏一覽》10卷又稱為駿河版,駿河版是日本近世三大官版之一,官版的興起是日本于數百年動亂之后振興文教的標志之一。駿河版還是首次用日本鑄造的銅活字印制的典籍,中國人林五官擔任技術指導。
2.天明一寬政年間
在尾張藩藩主、幕僚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群書治要》在這一時期獲得了大量刊刻和廣泛傳播。天明本《群書治要》是在尾張藩第九任藩主德川宗睦的主張下,由其世子、幕僚通力合作完成的。宗睦深知《群書治要》對日本平安時代繁榮做出的貢獻,然而元和本未得廣布,且由于排印倉促,訛謬多有,因此命二世子治休、治興與臣僚等校正刊印此書。
工作于安永年間開始,然而二世子先后于1773、1776年去世。安永六年(1777),高須藩的德川治行過繼成為尾張藩世子,繼承前二世子遺志,繼續刊行。參與刊印的人員有人見桼、深田正純、細井德民、岡田挺之、關嘉、南宮齡等,皆為尾張藩重臣、藩主侍讀、藩校明倫堂督學或教授。可見,尾張藩為保證校勘質量,集中了整個藩國最有學問的學者參與。
校勘時,“博募異本于四方”,“上自內庫之藏,旁至公卿大夫之家,請以比之,借以對之。”“內庫之藏”“公卿大夫之家”當指楓山文庫所藏的金澤本及九條家所藏的平安寫卷,四方異本指魏徵所引原典的傳世本。故校勘是以元和本為底本,與金澤本、九條家本進行校合,再與傳世原典相互對照。天明六年(1786)十月完成校勘,歷時約10年。
天明七年(1787)九月中旬印刷完成。據尾崎康,初印數量有五六十部(據《細井平洲書簡》)和三百部(據《名古屋市史》)兩種說法。刊印完成后,藩國重臣、校勘者、有關人員各賜一部。第二年,又有七十多位藩臣申請獲得此書。隨后多次補印。寬政三年(1791),尾張藩再次組織學者對原文進行了校勘,此次補印數量較大,此即寬政本《群書治要》。后享和、文化、文政年間,尾張藩又多次補印。在《群書治要》諸版本中,流傳最廣的就是天明本和寬政本。
《群書治要》在日本大量印刷后,日本學界注意到此書在中國已失傳,便積極將其傳回中國。首次回傳是在嘉慶元年(寬政八年,1796),據近藤守重記載,德川宗睦幕臣人見桼將五部《群書治要》委托其送予中國。守重與當時長崎地區行政長官中川忠英商議后,將五部中的一部存長崎圣堂,一部存諏訪神社,三部委托唐商館轉交中國。此次回傳的是寬政本。此本或其再刊本被阮元巡撫浙江時訪得,收入《四庫未收書》,上呈嘉慶皇帝。至此,在中國散佚失傳了近千年的《群書治要》重回故土。《群書治要》不僅再次傳入皇室,而且作為一部“佚存書”,在清末學術界,特別是在輯佚和校勘方面,產生了巨大影響。
3.弘化年間及近現代
紀伊藩也積極推動《群書治要》的弘傳。德川家康注重文治,尤其重視《貞觀政要》及《群書治要》,紀伊德川家欲繼承德川家康祖訓,使國老、諸司知書中大意,以有裨益于政治,于是刊印二書。在駿河版《群書治要》刊印230年后,紀伊藩用元和二年的銅活字再次刊印《群書治要》,弘化三年(1846)仲春竣工。
明治維新是日本近現代化的開端。明治二十四年(1891)三月三十日,金澤本《群書治要》入藏宮內省圖書寮(即宮內廳書陵部),由皇室永世保存。昭和十六年(1941),宮內省圖書寮以金澤本為底本,精細校勘,鉛字排印了昭和本《群書治要》。根據《群書治要解說》可知其刊行目的:《群書治要》作為治世寶典,對成就盛世具有重要意義,不僅李唐之治有賴此書,日本歷代皇室及公卿都極為重視。然而金澤本孤本流傳,且有大量異俗體字;而其他版本又多有訛誤,因此以金澤本為底本,將《群書治要》再次校勘出版。同年(1941),宮內省圖書寮還運用珂羅版技術復制了金澤本,復制本被分贈給日本各地圖書館及研究機構收藏,金澤本《群書治要》全面公開。
隨著日本政府建立公共圖書館,統一管理原官家及眾多私家藏書,藏于不同文庫的各種版本的《群書治要》也隨文庫的開放進入公眾視線,廣大學者得以近距離閱讀此書。此后,《群書治要》不僅在日本學界,也在中國學界收到了廣泛關注,書志學、出版學、校勘學、文獻學、版本學、語言學、歷史學及思想價值等方面的研究論文大量涌現。
結 語
《群書治要》在唐玄宗時期傳到日本后,不僅成為日本學習中華文化的重要典籍,還在此后的日本歷史中,從國家治理到思想傳播,從漢籍出版到學術研究,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它為中國保存下了這部珍貴卻又亡佚的“帝王學”教科書。
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日本前首相細川護熙向中國國家圖書館無償捐贈了36部4175冊漢籍,《群書治要》赫然在列。細川先生墨書題寫“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宣明了文化典籍的重要功用。
《群書治要》將中華文化的歷史淵源、獨特創造、價值理念等,簡要翔實地表達了出來,是一部匯集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的“次經之書”。書中所蘊藏的治國理政思想,特別是關于國家盛衰的經驗和規律,是歷經數千年考驗所累積的結晶,歷久彌新。正如魏徵所贊嘆的,此書實為一部“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的治世寶典。
【注: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群書治要》中的德福觀研究”的成果,批準號(19BZX123 )。為方便閱讀,本文略去引注】